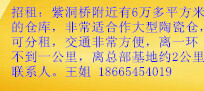相应地,品牌经理则要创建企业徽标,凝练公司口号,确定市场定位,制订市场份额增长计划。我们已经有一个徽标,没有口号似乎也无伤大雅,因此我决定集中精力解决市场定位和营销计划问题。我并不是第一个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
1999年年初,Google聘用斯科特·爱泼斯坦做市场顾问,希望他把公司的市场营销工作引入正轨,他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功终于证明拉里和谢尔盖就像吃素的人讨厌肥肉一样,对传统促销方式深恶痛绝。
他们拒绝了斯科特花几百万美元“创建品牌”的计划。在斯科特消失于茫茫夜色之后,他们指定辛迪担负起销售责任。
作为一名公共关系方面的资深人士,辛迪意识到通过用户口碑建立客户群更重要,而不是在广告荒地上层层撒钱建立品牌。Google有很好的故事可讲,而且在花钱做广告之前,利用公共关系可以收获很多容易采摘的果实。辛迪所需要的就是一点儿帮助。
辛迪后来回忆说:“1999年夏末,我们处于很困难的时期,没人愿意给我们回电话,也不把我们当回事。我们请了一个公司来做市场,但最终不得不让他们走人,因为他们只与自己投资入股的企业合作,而拉里和谢尔盖不同意这个要求。
这就促使我们改由自己来做组建一个小团队,积累一些专业知识,跟新闻媒体、分析人士以及相关领域有影响的人物建立直接关系。”不过,这里有一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经典难题:媒体不会关注Google,因为Google不是一个人人都在关注的公司。
通过用户口碑发展壮大,这符合拉里和谢尔盖对广告深恶痛绝的态度。他们经常嘲笑创业企业肆意挥霍,在热点体育节目中插播广告的行为,因为电视广告的效果无从衡量。你可能扔出去几百万美元,但是不知道是否会把一名观众转变成用户。工程师痛恨这种打着“品牌推广”旗号的低效率超额投入。
“品牌就是你停止前进的时候剩下来的东西。”这是工程师马特·卡茨在跟拉里和谢尔盖开会时听到的观点。只有当产品不再优于竞争对手的时候,品牌才会成为一个影响因素。等到那个时候,你其实已经输了。很长一段时间,拉里甚至拒绝使用“品牌”这个词,因为讲品牌似乎暗示单靠技术本身还不足以取得成功。
我的营销计划要改变这种状况。拉里和谢尔盖将会看到我们用各种方法引起用户及企业关注,并说服他们试用Google服务。我把脚搭在桌子上,眼睛盯着电脑屏幕,键盘放在膝盖上,开始打起字来。
“Google的最终目标是面向大众市场提供搜索解决方案,直接服务于终端用户,同时为目的地网站提供搜索技术支持。”我写道。然后,我开始列出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种种营销建议。
那么,计划呢?
我到Google上班的第一个星期,想跟辛迪要一份公司战略规划。她只是看了看我:Google没有战略规划。除了一些用以说服风险投资人放心投资的PPT(一种演示文稿程序)演示片,对于公司要努力实现什么目标,根本没有任何文字材料。这些内容都在拉里和谢尔盖的脑子里,他们从来没想着拿出来讨论。
我找到一份给风险投资商的演示文稿,马上就确信我们的战略目标就在开篇第一页上上面是一幅卡通画,企业家伯尼说:“你看这些搞搜索引擎的家伙,他们没有硬资产,有的只是让大家疯狂的软件。可是,他们的市值动辄以十亿美元计!当然,如果有人能用一个真正好用的智能搜索引擎半路杀出,那些公司一夜之间就会销声匿迹。”
我反复浏览演示文稿,其中粗略描述了Google的管理团队,列出了业务竞争对手,并提供了一些市场份额数据及投资预算,还有一页写着:“Google的秘密是什么?4年多斯坦福大学研发历程+Google.com研发经验+高素质团队。”答案已经明确。
关于Google的市场营销,演示稿里只字未提,因而我的计划就需要从头作起。我设计了一个金字塔状的图表示用户层次,最上层是“技术型用户”,最下层是“网络新手”。我制订了一个三阶段计划,可以分步骤推进。我提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技术型用户的市场规模有多大?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了吗?
我们需要开发新产品来吸引技术不是那么好的用户吗?调查结果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允许搜索专用数据库和域名注册记录,启动一项奖励热心用户的“Google伙伴”(Google Fellows)计划。我满怀信心地把计划书发给我们的管理团队。我没有提议花大价钱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而且强调的是采集数据的重要意义。拉里和谢尔盖似乎很喜欢数据。
“很棒,这个出发点很好。”谢尔盖回复说。的确,谢尔盖对我的大部分论据表示怀疑,但他没有把我的计划一枪毙掉,这足以表明其中蕴含的洞察力。拉里要更加保守一些,但他很喜欢我提出的问题,并且认为“Google伙伴”这个主意“棒极了”。
唯一的制胜之道
上交一个市场计划等着批准之后,我感到一丝轻松。不管我们的产品多么具有创新性,其他方面最终也得能跟产品相匹配,这是企业发展的通则。有那么一天,得通过市场营销为消费者创设一个明确的选择;有那么一天,我要迈步向前,大声宣布:“我已经整装待发,努力去干好自己的事情。”
那一天一直没来。
但这不是因为Google从一开始就一路领先,从来不会回头看看别人。提到公司早期的情形,乌尔斯说:“我们并不领先,实在不成气候。相形之下,Alta Vista和Inktomi则是两个庞然大物。Inktomi的服务器和我们在同一个数据中心托管,其规模是Google的20倍,比我们好得多。他们在墙上贴着自己公司的徽标,我们只是个努力做点儿新东西的小公司。我们的网页排名算法确实不错,但是速度要比Inktomi慢。我们只有往前追的份儿,他们的流量是我们的100倍。”
在我召集会议讨论自己提出的市场计划的后续步骤中,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Google公司到底有多脆弱,这倒很不错。如果有那样的认识,可能会让我充满错误的自信,以为我的建议书包含了所有答案呢。现在的情况是,对于我列出的计划大纲,我必须证明在每一步骤上进行投入的合理性。对于实施这项计划以及有些工作需要紧急完成的原因,我一一列表说明。
我说道:“我们自己的内部研究表明,竞争对手正在开始逼近Google的搜索质量,这是目前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所有搜索引擎的服务质量相差无几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依靠品牌把自己跟竞争对手区分开。”
敢为人先
Google公司1999年的假期聚会跟毕业生搞的离校活动差不多,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用白板装饰的屋子里。因为厨房的问题,饭菜上得晚,全都冷了。谢尔盖站到一个直径5英尺的红色皮球上发表祝词,但是他没法保持平衡,尽管他在当地的马戏团里上过培训课。他即兴开了几个玩笑,泛泛地说一切顺利,但是没有展望什么光明的前景,以便让我们相信明年开庆祝会的时候公司还会存在。
我和我的同事也不准“依照常规”做事。正如辛迪所说:“对于Google的市场营销,拉里和谢尔盖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程式化的做法。在我以前工作过的任何一家公司,当需要跟媒体见面时,总要准备一些信息,通常以PPT的形式提供,而且还要给他们一些相关资料。你事先应该接受专门训练,作好充分准备,以便对媒体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得体的回答。拉里和谢尔盖讨厌这种想法,拒绝照本宣科,也不使用PPT,而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这一点,新闻媒体很喜欢他们。”
负责线下营销的同事藤井莎莉对公司创始人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不太感冒。她锲而不舍地要求谢尔盖花钱作市场调查,恳求他引入外部代理,开展一场促销运动。她抱怨说:“他们就是不懂得大众市场对品牌建设的重要性,他得信任我们,让我们来做营销决策,让我们做该做的事。”
谢尔盖没问我和藤井莎莉对他这个主意有什么想法。他知道我们会冷嘲热讽。他转向苏珊,这是少数几个他能信得过的市场营销人员。Google在大学街办公的时候,苏珊就是公司小圈子里的内部成员,而且此前Google也租过她的房子。谢尔盖见过苏珊的家人(后来跟她妹妹结为夫妇),苏珊也能充分理解谢尔盖,因而不会立马否决他那些稀奇古怪的建议。
我们不应该按照过去的方式做事,我们不应该复制其他公司的做法,我们不应该等着有人告知企业战略,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战略的话。我们都是彼此独立的参与者,一道创建一个不遵圣训的紧密团体。我想我明白了:我应该找出问题并解决它们。于是我就这么做了。